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王诗颖 益阳报道
苏溪村的清晨,是被笔尖的沙沙声唤醒的。
锄头起落溅起的泥点、被炊烟揉碎的暮色、家中的柴米油盐,都带着平仄的韵脚。
没有人会想到,地处益阳安化县“边角”的这个小村落,诗歌会成为新时代的晨钟暮鼓。
▲山水间的苏溪村。(龚子杰 张必闻/摄)
这是一场静悄悄的变革,没有机器的轰鸣,也没有推倒重来的喧嚣,只有手指翻开纸页的声音。
87位,这是这个3497人的小村里乡土诗人数量;258首诗,这是《秀美苏溪》中所承载的乡土诗人的深情。
▲如今,吹拉弹唱和写诗,成为苏溪人日常的休闲活动。
当村民们学会在秧田里推敲平仄,在月光中寻找韵脚,他们才发现,脚下的土地不仅能生长粮食,还能生长诗篇;“耕读传家”的祖训,不仅是墙上的匾额,更是鲜活的生活本身。
“美丽屋场是典范,邻里和睦互相帮。清溪两岸田园美,可润苏溪万年昌。”——《苏溪赞》(节选)毛关达
苏溪村的诗,是从泥土缝里长出来的。
村口那棵已有240年历史的白果树,就是苏溪的“诗眼”。
相传,这棵白果树为乾隆年间安化县令余肇锡所栽。后来,村民们将此树比作魁星,凡有子孙参加科举,均会到此树前祭拜,以期高中。
耕读传家是这里世代相传的文化理念,“村子偏远,以前交通不便,所以我们更相信读书是改变命运的最好方式,从小就培养孩子们的阅读习惯和自主学习能力”。苏溪村党总支副书记毛关达说。
▲一位村民在白果树下读诗。
2021年,湖南城市学院驻村工作队的到来,给这个充满好学之风的山村带来了不一样的景象,村庄里的文化基因逐渐被激活。
到2023年第二批驻村工作队进驻后,队长张文弢发现,村里人爱读书爱写诗,那何不将他们的诗词收集起来,推出一本《秀美苏溪》诗集?
这个消息,在宁静的小村里引发了“震动”。
村里邀请安化县梅山诗社、县诗词协会举办诗词培训班,村民们自发拿起笔,写身边的人和事。
毛关达家开了一家小超市。午后生意清淡时,他就在货架旁写诗。
“以前写的都是打油诗。”毛关达笑着说,直到梅山诗社的专家来培训,才知道平平仄仄里藏着这么多讲究。
去年父亲的生日,他放弃了村里常用的充气拱门,而是作了一副对联送给父亲。老人读了好几遍,将这副对联好好收了起来。
毛关达说,自从开始写诗,他看苏溪的眼神都变了,“以前觉得苏溪的山真大啊,怎么走都走不出去。如今才明白,这些山不是困住人的屏障,而是守护村民的臂膀”。
▲毛关达对村里的青山有了新的理解。
“我一个高中文化的人,没想到有一天能有作品成书。”毛关达告诉记者,他也过了一把“文化人”的瘾。
他指着村里的青山说:“你看这些山,早中晚各有不同的模样,写诗就像给日子拍照,按下快门我们才能记录下这一刻。”
“壮志凌云典范型,勤劳俭朴美家风。牲禽养殖圈圈满,田土精耕岁岁增。”——《苏溪家风赞》(节选)邹胜阶
83岁的邹胜阶坐在新屋前坪,正将一束束竹枝捆成整齐的扫把。
村民说,他是苏溪村第一个写诗的人,后来村民学写诗,总要先来请教他一番。
邹胜阶的背有些佝偻,但走路依然矫健。
读小学三年级时,邹胜阶第一次触摸到了毛笔,便对它产生了兴趣。此后,村里大大小小的活动,总要邀请邹胜阶提笔。
30岁那年,邹胜阶成为村里的“赤脚医生”,从此,苏溪村的每个角落,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
▲邹胜阶临窗写诗。
2005年,梅山诗社邀请邹胜阶加入,本来是看中了他的毛笔字,却让邹胜阶爱上了诗。
“我觉得诗歌很美,和苏溪一样美。”邹胜阶说。
不懂如何写诗,邹胜阶就大量看书,“书就是我的老师”。在他看来,望闻问切与吟诗作赋并无二致,都是在琐碎生活中捕捉生命的韵律。
作为医生,他几乎认识村里所有村民,有时到村民家中,闲谈时会聊起写诗的好处。
“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了,留下的这些人连个像样的休闲活动都没有,我让他们多看书,学学《礼记》,写写诗,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丰富些。”这是邹胜阶最简单的想法。
邹胜阶在村里德高望重,他发现深受梅山文化影响的苏溪人,身上总有些“匪”气。于是,他在诗中写下“文化太低总觉蛮,诗词勤学莫偷闲”“勤俭持家遵祖训,子孙万代翼长兴”等诗句,勉励村民。
2020年,邹胜阶一家搬进新房子,他特意把离大门最近、视野最好的一间房作为自己的书房。
每天清晨,他先完成老伴交代的任务,然后一头钻进书房。宣纸铺开,提笔写诗时,窗外的云,正漫过青瓦。
▲邹胜阶在新屋前坪种下了各色小花。
临窗摆着书桌,邹胜阶从屋内抬头望去,自己种下的小花已悄悄绽放。
窗外是青山,屋内是墨香。
“以前想去大城市,现在离不开苏溪了。”邹胜阶说,现在每天过得很快,是他最钟爱的生活的样子,“写诗高兴,扎扫把也高兴”。
“十步园中见芳草,几家巷内出贤人。弦歌不歇朝朝有,琴剑长操日日新。”——《赞苏溪》(节选)邹石太
诗歌正改变着苏溪人的呼吸方式。
五月的苏溪村还浸在水稻禾苗的青气里,邹石太从田埂往家里走去,裤脚还滴着秧田的泥水。
▲邹石太随身带着纸和笔,随时记录看到的风景和感受。
他是苏溪村有名的诗人,身上还穿着几十年前儿子读小学时的校服,已经洗得发白。随身背的小包里,总是带着纸和笔,这是他的“文房四宝”。
家里的五六亩田地和鱼塘,占据了他早上和下午的几个小时。
三年多前,他还习惯在休息时带上扑克牌,去村里的小卖部扎堆,听着拖拉机“突突”的声音,一坐就是几小时。
两年前,听说村里要编写《秀美苏溪》诗集,这个消息像一颗石子投进了他平静的生活。
“写什么诗哦,咱农民哪懂这个。”邹石太蹲在门口擦拭着他的锄头嘟囔着,却在当晚再次翻出了他私下看过无数遍的《湖南诗词》。
邹石太在苏溪住了一辈子,但从来没有好好了解过这里的一山一水。为了写诗,他主动翻阅了苏溪的历史资料,将这里的人文与风光写进了诗中。
▲苏溪村农民诗人与大学生一起交流诗歌创作的体会。(图源:湖南城市学院)
在茂密的竹林中,邹石太寻访到了传说中的“将军石”。在“将军石”旁,他写下了“叶弯仑上将军石,镇守苏溪一条冲。岩山口上狮子守,上保君臣下保民”。
村里的土路变成了柏油路,他激动之余在诗里写道:“早年出门毛山路,如今公路宽又平。四湾八井全通达,大车小车忙不赢。”
书柜上的扑克牌积了薄灰,取而代之的是《唐诗三百首》和《四书五经》。每晚一到两个小时的阅读和写诗时间,成了比打牌更让他心安的“消遣”。
“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……”唐代崔颢的《黄鹤楼》是邹石太最喜欢的一首诗。不会说普通话的他,能用浓重的乡音将这首诗念得荡气回肠。
“我还没有去过黄鹤楼呢,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去看看。”邹石太紧张地搓着手,说出了自己的愿望。
当锄头与诗笔并肩,邹石太的生活有了别样的质感。
▲苏溪村一角。
起初,苏溪村的诗人只有3位。
听说村里筹备推出《秀美苏溪》诗集,苏溪的村民们开始主动执笔。到后来诗集成册时,村里写诗的人,增加到了70多位。
驻村工作队将诗歌创作与农耕文明相结合,在白果树下举办“春耕诗会”,在晒谷场组织诗歌沙龙,还将村部的公共区域改造成拥有4000册藏书的农家书屋,在村里修建了苏溪文化广场……
据最新统计,村里的诗人达到了87位。其中有村干部、“赤脚医生”、普通农民,年龄横跨古稀与中年,学历从小学到高中,他们都在诗歌中找到了与土地对话的新方式。
在苏溪村,写诗不是文人的专利,而是农民指尖的泥香。这里的每片砖瓦都藏着平仄,每条溪流都流淌着诗行。
这或许就是乡村振兴的动人模样:不是简单的物质堆砌,而是让文明的根系深深扎进泥土里,生长出属于这片土地的精神枝叶。
记者手记:
苏溪村是本土文脉复兴的样本
沿着蜿蜒的山路走进安化县清塘铺镇苏溪村,记者的第一印象是很美。
喀斯特地貌特有的峰林与溶洞在晨雾中若隐若现,三条清澈的小溪穿村而过,将这片土地滋养得绿意盎然。
这个山水画般的村庄,也有着它的“不得已”,没有出圈的旅游资源,没有厚实的产业支撑,地理位置偏远……这些因素,迫使苏溪人早早“知道了读书的重要性”。
据媒体报道,近年来,苏溪村走出了11位博士、34位硕士、181位学士,这是“耕读传家”的有力证明。
年轻人走出去后,和很多村子一样,苏溪村也面临乡村文化振兴的难题。
湖南城市学院驻村工作队的到来,让散落在田间地头的文化种子开始发芽。
当物质生活日渐富足,精神文化不足已成为部分村庄乡村振兴绕不开的话题。
苏溪村的实践提供了一种可能:文化振兴不能生硬地“植入”和机械地改革,而须因势利导地复兴乡土文脉,因地制宜地激活本土动能。
就像苏溪村口那棵已有240年历史的白果树,只有把根深深扎进泥土里,文化才有强大的生命力,乡村才能更好地走向振兴。
当人们发自心底热爱这座山、这条河、这个村、这棵树时,就能看到她另一个侧面的美。
比如白果树,又名银杏。
来源:红网
作者:王诗颖
编辑:罗倩
本文为湖南红网新闻频道原创文章,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。
本文链接:https://news.rednet.cn/content/646949/67/14982980.html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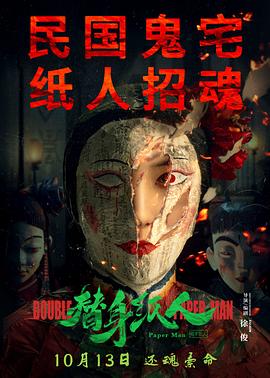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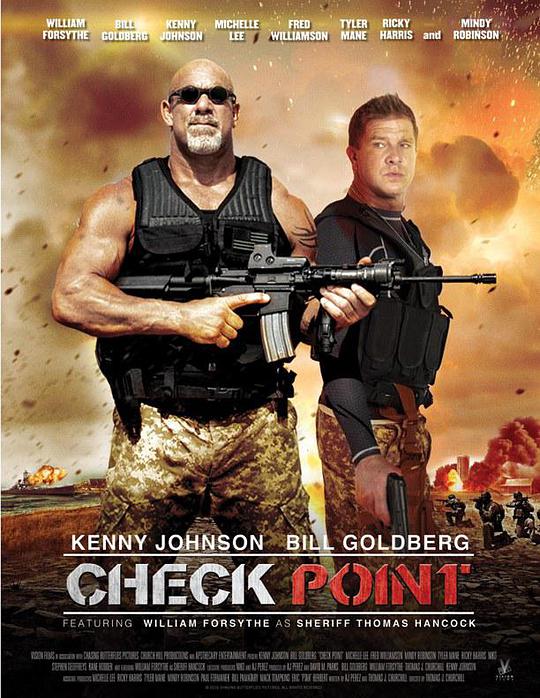
这篇文章分析得非常透彻,尤其是关于主播因为说十个勤天是爱豆鞠躬道歉的部分,给了我很多启发。期待作者后续更多的分享!
我在北辰区的一个项目中正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,按照文章中提到的方法尝试解决,效果很好。感谢分享这么有价值的内容!